
不少中国人对摇滚的最初记忆始于1986年:一个身背吉他的青年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走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献唱《一无所有》。1988年,导演田壮壮还拍了一部名为《摇滚青年》的电影,不过讲述的却是一个霹雳舞少年的抗争:敢于付出真正代价冲破桎梏、驳斥丑恶的行为,都被称为“摇滚”。茶余饭后不痛不痒的逆反、无理取闹,可别来掺和。

年少的骄傲与清高并不鲜见。不过,面对世界的条条框框,有多少人能保全个性?多少人能供养着年少的热爱?反观三十年后的中国摇滚“老炮儿”,太多的乐队和个人分崩离析,接而消失。2016年,隶属北京音乐家协会的摇滚音乐分会借“摇滚三十年”的名义成立:在场的“摇滚乐势力”们或是精神昏沉、或一本正经、略显富态。由于特邀名单里还有于谦,有人忍不住将分会调侃为“北京摇滚曲艺协会”。

“摇滚,你玩它有啥用?”
摇滚,没必要陪伴一生吧?年少时的大声疾呼、义愤填膺,到了沉甸甸的中年,是时候转化为内敛的洞见、平静的思考?不然继续折腾,这能行吗?又“有啥用”呢?

成立于 1982 年的日本视觉摇滚始祖X-Japan。
在洛朗与马修看来,摇滚仍旧兴盛,并依然青春。这两个外表“尘土飞扬”的“摇滚农夫”在24个国家参与过800多场演出。不过,从万人的亢奋演出场面“乖巧地”退回农场的过程中,似乎缺了点什么滋味。耀目的光环哪去了?两人更像是敬业而固执的工程师:二十年的老搭档,如费力燃烧青春的新手一样,在农场地下室兢兢业业地排练,寻找火花。

洛朗和马修
两个人憋着一股劲,不愿沦为“墙上的另一块砖”(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名言):年少时,他们受的教育,是让其“成为工程师、数学教师的”。出于对摇滚的迷恋,二人奋不顾身地选择了乐手道路。从八人的乐队到两人的搭档,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规划,似乎都是为了不过度依赖音乐工业,以换取追逐目标的资格。

佯装愤怒不如回家养鹅
精神鸦片也好、无聊消遣也好,也许摇滚是个什么玩意儿已不再那么重要。比起掏心掏肺的创作,太多音量足够大的歌曲就能随随便便地催生肾上腺素。谈论毒品、绝望、自我放逐的“不良青年”把张扬跋扈的姿态做足,招摇撞骗般地将“摇滚精神”延续下去。

作为一种商业手腕,乐手的“坚持”更像是种尴尬矫情的卖相:“他们只有在安全时才勇敢、在免费时才慷慨、在浅薄时才动情,在愚蠢时才真诚”,米兰•昆德拉的刀子嘴如是宣称。熙熙攘攘的听众或是为了信仰、抑或是发泄聚到一块空场地上嬉闹。总归是你情我愿。

当所有智慧和生活经验无法驾驭生活时,洛朗与马修退回到农场的泥泞中喂鹅,用韧劲不断写歌、出专辑。他们内心中的那个年轻人对社会的每个命题仍有自己的理解和批判,而中年人的外在,则负责用更强的能力和技巧,使内心得以完整淋漓地表达。

“只要能自给自足,我们愿牺牲一切”
农场里没有什么都市想象中的田园诗意:那里的生活井井有条,每周、每天的时间都得提前细致地规划好。洛朗的舅公耐心地手把手教授务农技巧,他们也将这些日常运作细节、养殖、清洁技巧烂熟于心。
起初,邻居们难免对“半路出家”的二人持怀疑态度,把他们当做暂时来“玩票”的嬉皮士。毕竟,“嬉皮”早已成为一种无毒无害的时尚、点缀,被有序地组织进主流阶层的轨迹之中。特别当两人从日本巡演回来,打算种水稻时,不少人更是难掩嘲讽的语气。两人将周遭看法照单全收,然后依旧我行我素。

克服了生存压力后,二人对经营农场这一行为还有着更远的思虑。虽然对于劳碌的大众来说,这未免杞人忧天:“我们在日本、中国、拉美一些国家巡演时,深刻觉得,人的源头将会枯竭”、“人们连种番茄都不会”。在他们眼中,人们像早已根茎萎缩的花草,一代一代被切断了与大地的直接联系,而生命之源会因此断绝。

乌托邦中的世界公民
他们从世界巡演中寻找新的动力。音乐是普世的语言,此言不虚。当命运让不同乐手的道路交错,各自都在影响彼此的人生。也许成千上万听众的心绪也会有改变?不论如何,摇滚农夫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我们是世界公民”。

农夫们看上去平凡、平静。他们没有焦躁不安地频频回首、急切地证明自己,也未显露出愤世嫉俗的消沉。毋庸置疑,他们是幸运的:既不用忍受远离家乡、四处漂泊的不安,也无需领受困守小镇的不甘。他们的生命没有因背井离乡或身处农场而一分为二、迟疑疲倦:它合为一体,非常完整。剩下来要做的,就像尼尔•杨在歌里唱过的,“让我们继续在自由的世界中摇滚吧。”
(欧洲时报/ 杨雨晗)
编辑:海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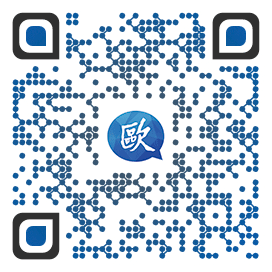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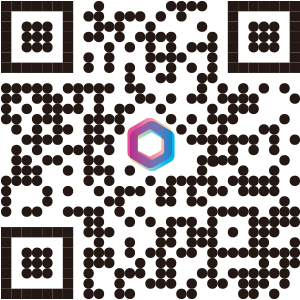 扫描关注微信公众号
扫描关注微信公众号
评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