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电灯环绕散射产生的阴影下,一群年轻人坐在靠近英吉利海峡高速公路的草地上,零散几个人在附近砾石上踢足球。旁边的化工厂还开着工,烟囱上的浓烟冲着灰色的天际线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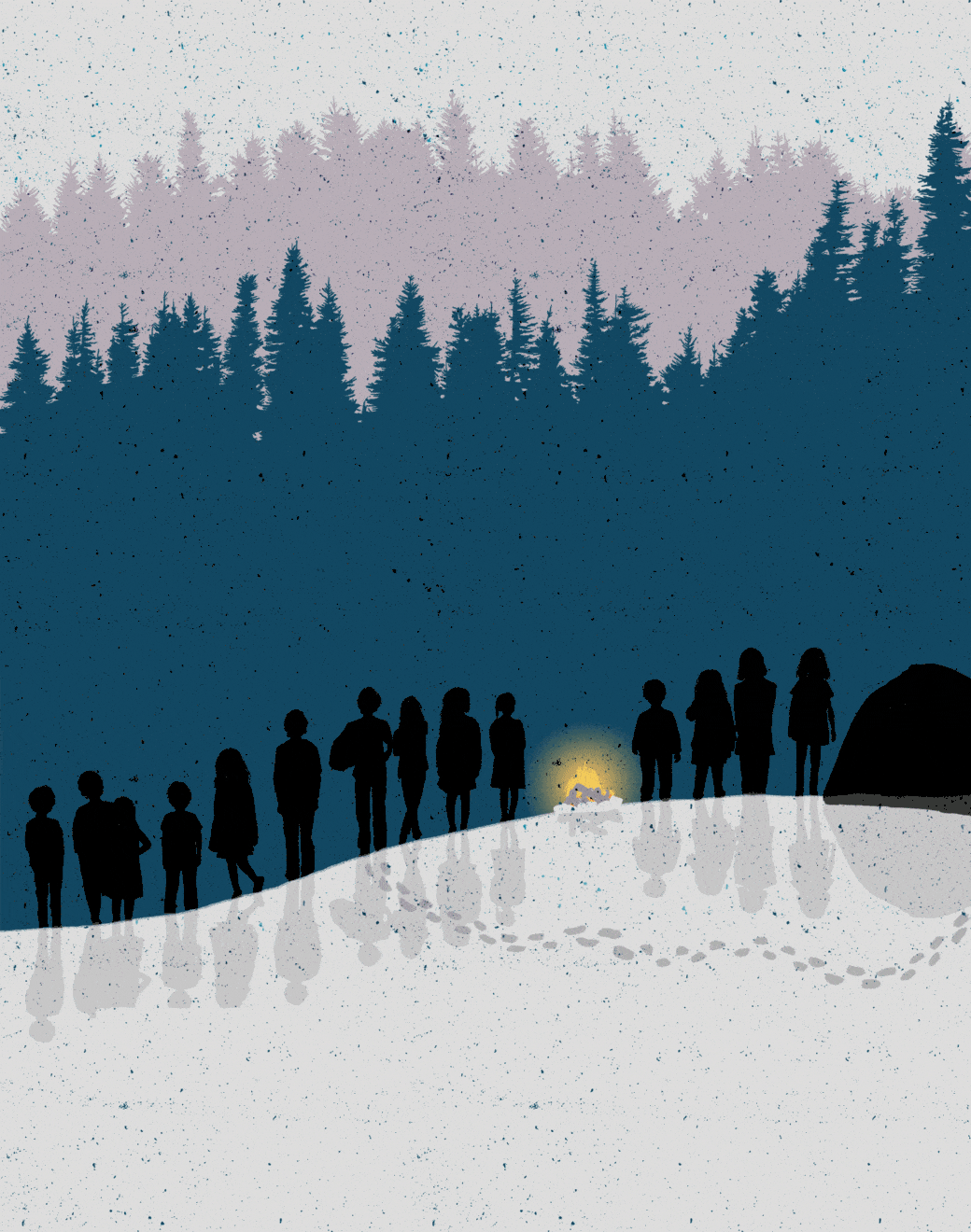
下午6点在加莱营区的紧急分发点,等待分发食物的多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些未满18周岁的年轻人,此刻没有家,没有庇护所,也没有监护人。许多人等在这里领这一天唯一的餐食,来自法国的宪兵警察在一侧维持秩序。
17岁的Daniel坐在其中一个沙丘上,双脚拖着鞋,吃着一顿摊在塑料碟上的米饭。Daniel告诉作者,他晚上一直在尝试睡着觉,但与这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几乎无法入睡。通常是在晚上,警察会突然穿进森林,然后各个方向乱窜,导致许多人每个晚上都无法入睡。
最明显的抱怨是这句,“这些警察每天晚上都在燃烧睡袋,他们似乎都不用睡觉。”
拿胡椒喷雾喷撒我们,生活一下子就变得很艰难,我现在就在想着哪天可以去到英国。另一个年轻人也加入了谈话,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需要自由,但看不到什么解决方案。

加莱的难民营已经被清理了6个月,在那次清理中,共有10000名难民被清理到不同的地方。但据Help Refugees这个慈善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在这个区域还活跃着200名左右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人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比如厄立特里亚,苏丹,埃塞俄比亚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些未成年人仍然希望能够穿过设置森严的边界前往英国。

而来自厄立特里亚这个有着无限期服役、强制劳动制度且被人权观察社评为世界上最压迫的政府的Daniel对于前往英国有着坚定的决心。“大概有15次了吧,警方有次把我放进监狱一个月,有次是放了45天。”“我想要去学习工程师专业,这对心灵有好处,而且一个新的移民族群也会被创造。”
一些想要去英国的未成年人是因为在英国有家人,而他们也有加入的权利。即便根据内政部放出的消息,来自加莱地区大约有750多名未成年人已经被安置在适当的营地,但加莱的Help Refugees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家庭团聚的进程是如此复杂冗长,这使得人已经失去对系统的信心以及通过合法路线安全抵达英国的可能性。
而一旦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开始考虑通过其他方式到英国寻找避难所,他们又将面临非常巨大的危险。
志愿者们也会抱怨,警方有时会摧毁他们给这些难民的物品。毯子通常不是因为下雨而丢失或毁坏,而是因为警察使用胡椒喷雾而不能使用。他们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往外发放200个毯子,累积起来,这个数量远远超过加莱营地彼时10000人的数量。
正在排队领餐的Beba只有13岁,他说自己在英国有一个姐姐。他想要学习,想要有社交生活,想要踢球。而且最喜欢的是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我想踢足球,但这里没有足球,没有体育场,只有石块。”长大以后想要从事一切类型的工作,但现在却被警察搞得筋疲力竭。

15岁的Solomon Ayuub来加莱难民营只有4个月,也就是说他是在这个营地被清理之后抵达的。今年的斋月是他离开家后的第一次守斋,他有家人在英国,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长大之后想要学电气工程专业。他睡在丛林中,一个背后只有森林没有营地的光秃秃的存在,警察经常会跑过来拿走我们的睡袋。当他睡在公园中时,又会有宪兵过来,先是听到“Allez Allez”的呼喊声,接下来的串联动作就是被喷胡椒。
14岁的Thomas向人描述他在厄立特里亚的家,模仿有人拿枪并射击的样子。他睡得很少,“我非常害怕,我是人呀,不是动物。每晚我都在哭,我思念家人。”
17岁的Samira同样来自厄立特里亚,作者在法国北部其他地方碰到的她。她刚刚消失了2个月,引起了严重的治安隐患。离开厄立特里亚后,Samira在4个月的时间中历经了苏丹、撒哈拉沙漠、利比亚以及地中海,希望最终能够到达英国寻找在伯明翰的亲戚。她到达加莱营地的时间是16年7月。
“一点都不好,我不能睡觉,每天都很累。”她最初到达的是加莱有些肮脏的丛林营地,接着10月份推土机开进来开始拆除,Samira和其他孩子一起被安置在转换的集装箱中。根据“难民援助条例”,11月份的时候她被告知可以根据“配偶修正案”的细则在英国避难。但是当她去搭公车时,却被告知不能上车。她就这样被不明原因地遗忘掉了。
Help Refugees也不能评价究竟发生了什么。接着Samira被送到了巴黎南部约三个小时的住宿中心,在那里虽然她又认识了新的朋友,但关于她是否能够前往英国,还是需要一直等待。
但经历这种情况的年轻人通常是顽强的,他们想做的就是在某处重新开始生活。于是在Samira听说仍然有人从法国北部穿越去英国,她立马离开了住宿中心,前往了距离加莱70KM的营地。在那里,她联系了当地工作的慈善机构的难民青年服务处,并解释了自己目前尴尬两难的状况。慈善机构认为Samira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当这些帮助难民的志愿者在1月份到营地寻找她时,她已经消失了。
6周以后,厄立特里亚社区志愿者在加莱附近的另一个营地找到了她。腿上与身上带着瘀伤,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痛苦、疲惫。她去了巴黎,以为从那里有机会去英国。在那里,她和一些其他女孩睡在La Chapelle的一个帐篷中。同样是在那里,她被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告知,如果她想留下来,就必须“工作”。
帮助难民的法律顾问Sabriya Guivy在Samira被找到时和她进行过交流,那时的她经历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痛苦,她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从一个地方接着又跑到另一个地方,也许只是她的耐心被磨没了,所以选择了离开。
Samira最终在法国国家保护下获得了临时庇护,这意味着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房子居住。慈善机构给了她一个新的手机和SIM卡,以防止任何可能曾经拥有她号码的人再次接触她。
而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一个欧洲未成年难民身上。
当作者见到Samira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自己终于在被公共汽车抛弃6个月后可以重返英国。当大家约好在一个城市的小广场见面时,她热情地拥抱每一个志愿者。她穿着灰色慢跑裤子与黑色芭蕾上衣,扎着马尾辫子,带着大家去她最喜欢的公园。
自从Samira听说了好消息后,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为生活即将发生的变化感到兴奋。她期待着上学,并表示自己一直想学习地理学,她还期待能够学习园艺。当被问及当她长大时会做什么时,她回答“想要帮助像我这样的人”。

在加莱营地被拆毁之前,这里被形容为“有害的细菌滋生地”。同时,许多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也带来了众多不同的问题。在营地与定居点得到清除之前,这些问题将一直增长,直到法国为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足够且充分的解决方案。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这里还有数量巨大的年轻人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下,没有制度的约束,有的却是在他们看来粗暴威胁的警察与极右组织的抗议。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数字,全球难民和移民儿童人数已跃升至历史新高。自2010年以来增加了近5倍,至2015-16年度已经有至少30万人。
来自Help Refugees机构的McHugh说,整个帮助难民寻求庇护的过程会令人非常失望。年轻人有权知道他们究竟在遭遇什么,但实际情况通常是暂住在加莱营地的未成年人在求助无果的情况下打电话给英国的家庭,而英国的家庭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过程让人心生倦怠。
这些机构原本希望能够帮助至少3000名未成年难民受益“配偶”修正案,但目前只有350人通过这项法案去到英国。而5月份英国政府也在低调中宣布中止对这个计划的承诺。与这一低调中止极为反讽的是,是英国政党大选之前的宣言,比如保守党的宣言是,“只要有可能,英国政府将会向受冲突和压迫影响的世界上一些地区的人提供庇护,而不只是向英国人提供庇护。”
作者和McHugh专门跑去看了位于加莱的配送仓库,这里由位于本地的所有难民服务组织共享,包括为难民散发衣物、床上用品与卫生用品以及提供餐饮。但这些组织并不希望有人在这里拍照并将其曝光,因为接着而来的是极右组织的抗议。

加莱几乎所有寻求庇护的未成年人都是无人陪伴状态的,McHugh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为难民引入积极的榜样并与他们交流,他们邀请年轻的Oromo(奥罗莫人是非洲东部的一个民族)的专业人员或在巴黎求学的厄立特里亚学生们。并鼓励他们考虑也许可以在法国寻求庇护,并获得居留许可的可能,而不是一味苦苦等待跑去英国,甚至可以在18岁成年的时候选择是否愿意返回原籍国。

为了减轻这些未成年人在面临未知生活时焦虑的情绪,志愿者也尝试为他们组织一些桌游。偶尔也会组织一些主题游乐,但偶尔遇到的沮丧情况是,很难保证这些生活在加莱地区的未成年人不受到种族主义形式的歧视,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而法国当局在加莱营地拆除之后,也宣布不再对这个区域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以难民只能通过义工组织获得食物、衣服、毯子。场景再次回到文章最初,宪兵队将他们的帐篷拆走后就离开了,此时阴云密布。
有些人还保留着自己的帐篷,有些人拿起毯子和披风向森林深处走去,继续在雨中面对另一个夜晚。

(翻译自buzzfeed,作者Aisha G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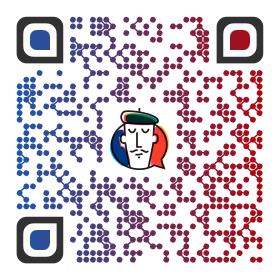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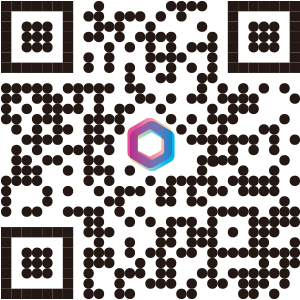 扫描关注微信公众号
扫描关注微信公众号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