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诗人孟浩然有一首五律《过故人庄》,诗写得朴实平淡“,淡得看不见诗”,像聊家常一般,可是字里行间诗意盎然,且散发出浓浓的人情味。
诗的一开头就说:“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老朋友请吃饭,诗人一请即到,自然不是什么盛宴,没有那么多讲究,不过杀了只鸡,备了些家常饭菜而已。
可见那个时候,在中国普通人家,鸡就是款待客人的一道常见菜肴了。

就一般的食材而言,我总觉得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对鸡有些偏爱,普遍认为鸡是“好东西”,比猪肉的档次要稍高一些,且更富有营养。逢年过节,家宴中最后端上餐桌的一道大菜常常是沙锅炖鸡,又浓又鲜的汤里卧着一只整鸡,讲究一些的人家还要加上一只猪蹄膀。
大病初愈,要喝鸡汤补补身子。产妇分娩,大补的食品更是离不开鸡。既然鸡是很多人钟爱的一味好菜,那么在一向看重交友之道的中国人眼里,杀鸡待客就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我也喜欢吃鸡,不过在巴黎一般超市里买来的鸡虽然个头硕大,但肉质粗砺,无论烧汤还是做菜均不见佳,吃到嘴里味如嚼蜡。至于大名鼎鼎的肯德鸡,说是用特制配方烹炸而成,外表一层倒也香脆,但表层以下的鸡肉部分淡而无味,尤其是厚厚的炸鸡胸脯,简直难以下咽。每当此时,不由得又会想起和吃鸡有关的一些琐事。

妻子的白斩鸡
在上海工作生活的那些年间,我们晚饭的餐桌上常常有一道白斩鸡,那是妻子的杰作。妻子做的白斩鸡色泽滑润鲜嫩无比,百吃不厌。我看她做起来似乎并不那么费事,鸡放入水中白煮,然后切块装盘,再配上精心调制的蘸料,实在是上好的美味。不过,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实地操作却并非易事。
先要大火烧开,继之小火煨制,关火后还要在锅里焖上片刻,无论是烧是煨还是焖,火候一定要仔细掌握,这就要看厨师的经验和本事了。倘若火候不到家,其结果就会像台湾的一位美食家说的那样,“一样的白斩鸡,有的意象分明,一入口就像聆赏曼妙的音乐,有的咬起来像咬皮包。”

白斩鸡
其实,白斩鸡只不过是一道极为普通的菜肴,在中国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几乎随处都可以见到,它既是家宴中的一道必备的冷盘,也是各地大大小小的餐馆里常见的一味小菜。郭沫若在他的自传里曾写到他童年在县城读小学的时候就学会了喝酒抽烟,那时他最喜爱的下酒菜就是白斩鸡,这是那座小县城里最普通的馆子里也能吃到的美味。
“嘉定城的白斩鸡是最有名的,那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 把鸡在白水里囫煮,煮熟后切成肉片拌以海椒,酱油。就这样简单的烹调法,却是最可口的佳肴。” 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这味“最可口的佳肴”,可见这道菜在郭老心里的份量。至于嘉定的白斩鸡是否“最有名气”,那就见仁见智了。

芙蓉鸡片
不过,白斩鸡虽好但也略嫌不足,我觉得它似乎只宜下酒,而像宫保鸡丁、芙蓉鸡片、椒盐鸡块等等,则是下酒固好,佐饭亦佳。如果要开列出像这样一类用鸡制作的菜单,我想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长长的一串。而在中国各地旅行,几乎每到一处都可以吃到极富当地特色的美味鸡肴,要把这些全部记下来写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宫保鸡丁

婶母的辣子鸡
这里我想说一说辣子鸡,辣子鸡也称爆炒辣子鸡或清炒辣子鸡。我说的辣子鸡不是哪一家餐馆的招牌菜,而是我的婶母做的一道家常菜。不知多少次我曾亲眼看着这位婶母做这道菜,从杀鸡,剁块,翻炒到装盘,她使用的食材佐料跟他人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在我看来,她做出来的辣子鸡,任何一家餐馆都无法与之相比,真称得上色香诱人滋味无穷,几十年后犹觉口中留有余香,无法忘怀。
她选用的是只有一市斤左右的小公鸡,宰杀后放入沸水中翻滚片刻,拔毛洗净剁成小块,然后在锅里重油大火炒就。除了葱姜蒜之类佐料之外,她用的配菜似乎只有两只青辣椒,可是通过她的一双妙手的翻弄,普普通通的鸡块竟成了一道绝佳的美味。

辣子鸡
后来我曾在云南,四川,北京等地的餐馆里品尝过各种不同的辣子鸡,有的是鸡块,有的是鸡丁,有的上面还堆满了厚厚的一层红辣椒,令我望而生畏。
说真的,这些个所谓的辣子鸡和婶母的杰作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味道差得实在太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阔别多年后我有机会再次见到这位婶母,那时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她一见到我,便立刻吩付家人去菜场买来一只小公鸡,她不顾高龄亲自下厨动手,一阵忙活之后端上来一大盘久违了的辣子鸡,浓香四溢,令人馋涎欲滴……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婶母已经下世,如今我远居海外,深知心中的这道美味辣子鸡已成绝响,只能在记忆里慢慢回味了。

符离集烧鸡的记忆
说起鸡的种种吃法,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还有烧鸡,我以为这种烧鸡的味道远远胜过巴黎随处可见的烤鸡。还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常带着我乘坐火车在上海和徐州之间往返奔波,每当列车停靠在符离集车站时,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光景,父亲总要急匆匆下车买一只烧鸡,有时还要搭上一包卤鸡杂。
火车开动后,我们便开始享用这色佳味美的烧鸡,虽然是在行进的火车上,父亲有时还是要喝上一杯,也许在他看来,有肴无酒应该是一种憾事。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了符离集烧鸡的大名,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每次我乘坐火车经过这座小站,都忘不了再买上一只大快朵颐。唯有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年月里是个例外,那些年头人们连吃饭都很困难,哪里还有烧鸡的踪影。

还记得1964 年的夏天,我在大学读书,正值暑假期间闲在家中。我有一位兄长在铁路上工作,有一天他对我说要去符离集出差,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我欣然应允,于是有了一次难忘的符离集之行。说是难忘,自然主要是指它的烧鸡。那时的符离集城镇很小,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就像一座集市,没有什么大商场大酒店,但却可以看到很多专卖烧鸡的店铺。
哥哥带着我走进一家烧鸡店,说这家的烧鸡最为正宗。记得那家的店主是一位爽朗的中年妇女,她似乎和哥哥很熟悉,我想哥哥大概是这里的常客吧。我们刚刚坐下,店主人便托着一只大盘走过来,盘中放着一只硕大的烧鸡。

烧鸡不是切开来吃,而是用手撕着吃的,因为鸡肉烧得又酥又烂,极易脱骨。果然,只见哥哥提起鸡腿稍稍抖动了几下,大块大块香气扑鼻的鸡肉纷纷落下,刹那间便堆满了整个盘子。我捡起一块放进嘴里,但觉油而不腻酥软可口,咸淡适中鲜味醇厚,比起车站站台上出售的烧鸡味道更佳。那天中午我和哥哥尽情享用了一顿美餐,心想此行果然不虚,总算见识了正宗的符离集烧鸡。
后来,上世纪90 年代末我因公务从巴黎飞北京,几天后又乘京沪特快列车转赴上海。途经符里集车站时正值深夜,列车呼啸着一闪而过没有停靠,望着车窗外深沉的夜色我不禁有些怅然,想起了那次符里集之行,还有许多往事...... 再后来,我听说符里集烧鸡已经成了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符里集市镇也已大大扩展,旧貌换新颜了。
说到这里,这篇闲言碎语也该打住了。
◢编排:miu
◢撰文:王聿蔚
◢来源:《食尚亚洲》1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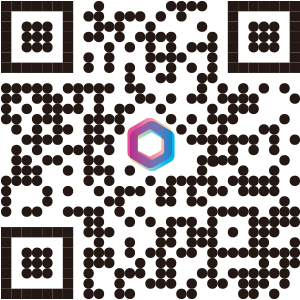 扫描关注微信公众号
扫描关注微信公众号
评论 (0)